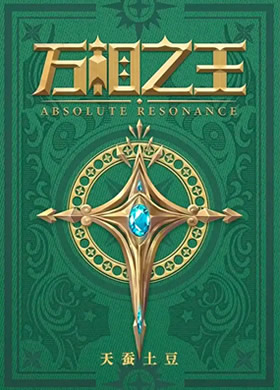徐宝藻目瞪口呆,转头问道:“你灌醉他,谋财还是谋色?”徐凤年没好气道:“我哪里知道他喝桂花小酿也能醉。”徐宝藻皱眉道:“咋办,就把人家晾在这里?”徐凤年犹豫了一下,喊来那位如临大敌的店伙计结账,不忘连同韩横渠那桌酒菜一起付了,后者兴许是迎来送往多了,擅长察言观色,没把徐...
身在市井却心在江湖的店伙计点了点头,趁着那位抠门店掌柜正忙着跟一位丰腴妇人搭讪,抢过年轻剑客手中的那杯酒,喝光了后赶紧还给这位酒楼的头等贵客,然后丢了个会心眼神,屁颠屁颠小跑离开。对这位店小二而言,这一天,因为这杯酒,就又是个好日子了。不过店小二突然转头提醒道:“韩公子...
徐宝藻说她很小就想要有一头毛驴作伴,看着夕阳西下,春风里路旁开满桃花,一路漫游,随心所欲,从春风看到秋风,从南到北,一直从青葱烂漫到白首苍苍。徐凤年对此不置可否,世间少年往往志向如大赋,少女情怀则如词曲,他并不陌生。这一次他没有带着她从头到尾都是御风凌空,而是遵循她的意...
徐凤年思量片刻,问道:“是陈芝豹?还是顾剑棠?”江斧丁笑眯眯道:“再猜。”徐凤年斜瞥了一眼这位半寸舌元本溪的嫡子,“一如当年初次见面,还是好像额头上贴着欠揍两个字。”徐凤年想了想,“应该是‘找死’更准确。”江斧丁微微扬起脑袋,好似追忆往昔,“这些年我待在京城,很多次假设...
她不知道,因为她的缘故,牵一发而动全身。风雨自八方而来,向他而去。洞天福地的地肺山,群贤毕至。山不在高,有仙则灵。约莫十位衣着气态皆迥异的男男女女,匆匆而来,姗姗而来,飞掠而来,蹒跚而来,踱步而来,骑牛而来。南边,有位模样清逸的年轻儒生,背着棉布行囊,露出书画的轴头,或...
徐凤年带着少女在一座山的山脚停下,身后是一条潺潺而流的灵秀河水,那座山算不得高,左右有山丘如同门阙,在两人脚下是一条大幅大幅青石板铺就的登山道路。徐宝藻环顾四周,如同一位掉书袋的老学究,“这地儿,在地理堪舆上好是好,却不拔尖,根据西楚国师李密的那部考古志,终南群山以雁回...
徐凤年瞥了眼体内气机迅猛流转的年轻人,江湖上有个好师父的“高二代”多如牛毛,如韦弘极这般却也算凤毛麟角,打趣道:“怎么,要拿师父的名头压人?”韦弘极眼神真诚,摇头道:“不敢,也不愿。”徐凤年撇了撇嘴,不置可否。一位少侠既没有韦弘极这份眼力,也没有韦弘极的耐心,大踏步向前...
京城,江南,西北,两辽,处处有小娘偷悬挂像,日夜思量着那位风采卓然的神仙中人。不知何时,那个锦衣华服的孩子鬼鬼祟祟来到了徐宝藻身后,猛然前冲,试图双手环住少女的纤细蛮腰,大概是想打着天真无邪的幌子揩油。不曾想被迅速侧身的徐宝藻一巴掌狠狠摔在脸上,响声清脆,刹那间整座观南...
既然那个家伙没有催促,徐宝藻就乐得一块一块石碑仔细观摩过去,看她的架势,好像恨不得要扛起那些沉重石碑下山。事实上历史上还真有书法痴人做过此举,耗费巨资雇人将十数块碑文运送下山,也许初衷是希望能够更好保存石碑,不至于年年遭受日曝雪冻,但可惜恰恰是碑林依旧屹立至今,那些藏在...
徐宝藻放回文稿,眨了眨眼睛,“你知道白莲先生为何不肯入京当官吗?”徐凤年静待下文。徐宝藻双手负后,走到窗口,转身背靠墙壁,“凉党骤然得势,满朝惶恐不安,必然抱团取暖以抗凉党,绝不可让从西北边陲走出来的文武官员形成大气候,不说元气大伤只会做墙头草的青党,恐怕连江南士子集团...
徐宝藻轻声问道:“道教三十六洞天,山中当真有洞室直达天庭吗?在七十二福地修行,善缘福报当真得天独厚吗?”徐凤年淡然道:“千年以降,此事信未必有,不信未必无。只是以后百年千年,兴许是当真没有这种事了吧。”徐宝藻听得如坠云雾,但是抹不开面子刨根问底,嘀咕道:“又装神弄鬼。”...
两人沿着青石板小路走出三四里山路,入了道教祖庭龙虎山的地界,跟徽山山脚的喧闹就有了云泥之别,人迹罕至,格外幽静深远。当他们看到一座翘檐尖尖的小亭子,徐宝藻快步走去,等到走近,才发现有位头戴帷帽的女子游客,早已坐在亭中长椅上,右腰叠放长短双刀,身穿短打紧身的合身衣衫,身形...
徐凤年有些心情复杂,拒北城一役之前,曾经与她约好了将来有一天一起去找姓温的喝酒,不知为何她似乎反悔了,上次徐凤年去那座小镇邀请过她,递去徽山大雪坪的口信,便如泥牛入海。很久就有眼尖的江湖豪客瞅见徽山之巅的异象,渡船上一时间哗然一片,就连徐宝藻都扬起脑袋,痴痴望向模糊不清...
一夜之间,两人就来到那条歙江的江畔渡口,已经能够遥遥看到徽山牯牛大岗的轮廓,当然还有与之对峙的龙虎山。如果不是为了照顾少女,甚至都不用等到天亮,他们就已经在徽山大雪坪了。两人在一座渡口等待一艘两层楼巨大渡船的启航,如今徽山是名副其实的江湖圣地,大雪坪观雪,也成了好事者嘴...
少女王生在看到师父的眼神后,迅速关闭剑匣,重新无声无息。师徒二人正是徐凤年和王生,其实不算凑巧,徐凤年的确要救人,不是什么观海徐氏的胭脂评女子,而是那个更换了姓氏的少年,在祥符年间的早期,当时这个十来岁的孩子应该姓孙才对,爷爷是西楚老太师孙希济。西楚复国的尾声,大官子曹...
哪怕年迈马夫竭力阻挡,可仍是不断有徐家子弟走下马车,一男三女,男子才十五六岁,年纪最长的女子是妇人模样,抱着一个粉雕玉琢的稚龄女孩,身旁怯生生站着一个肌肤微黑的粗衣丫鬟。高亭侯心头一震,策马前冲,一槊打烂马车车厢,空无一人,转身用长槊槊尖轻轻搁在那名妇人肩头,眯眼问道:...
圆月悬空,人间头顶如挂玉盘,月色如水。一队百余披挂精制甲胄的骑军从官道转入小路,雄劲马蹄好似踩碎了泥路上的月光。这支骑军人人佩刀负弩,精悍异常,为首魁梧骑将竟然斜提了一杆长槊,在月色映照下,清晰可见男子那条斜跨整张脸庞的狰狞疤痕。马槊在春秋之后就极少出现在沙场上,这种兵...
那一刻,她甚至觉得就是今天嫁给了宋秋木,只为了将来能够每隔几年就看到这女子刀圣一两眼,那她这辈子也算值了。这不单单是高堂燕势利眼,而是童山泉如今的江湖地位,太高太超然。相比太白剑宗的陈天元肆意挥霍天赋,自甘堕落,童山泉在武道一途的勇猛精进,一日千里,显得尤为令人瞩目。据...
年复一年看潮人,直到白头看不足。从春秋到永徽,再到祥符,直到如今的阳嘉,大潮年年有,白首之人年年走,就如春秋剑甲李淳罡之于江湖,徐家之于西北边塞,大雪龙骑之于北凉边军,也会随着老人们的渐渐逝去,而逐渐消散在滔滔江水之中吧?那个下场凄惨的广陵王赵毅,在那场平定西楚的庆功宴...
年复一年看潮人,直到白头看不足。从春秋到永徽,再到祥符,直到如今的阳嘉,大潮年年有,白首之人年年走,就如春秋剑甲李淳罡之于江湖,徐家之于西北边塞,大雪龙骑之于北凉边军,也会随着老人们的渐渐逝去,而逐渐消散在滔滔江水之中吧?那个下场凄惨的广陵王赵毅,在那场平定西楚的庆功宴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