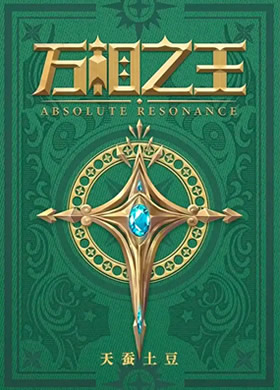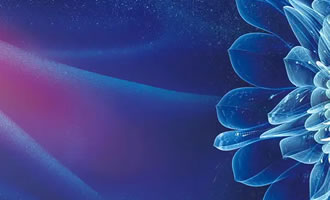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,而是这并非一具尸体,那人缓缓睁开了惨白色的眼睛。牟中流拍了拍崔牧之的后背,递给他两颗丹丸,“沉香木丸,塞在鼻孔里,可以克制异味”。满室都是血和腐烂的味道,但是在这惊悚的一幕前,崔牧之的鼻子都迟钝了。“这是你的同僚,西瀛海府都统洪秀山,”牟中流低声...
搞到票又有什么用?我和部队签了军事服务协议,如果我走,就是逃兵,会被送上军事法庭。我和大猪二猪开过玩笑,说我这种合约叫做死当,不能赎回。从落笔的那一刻,我就知道。走出候机大厅,一下子安静起来,天空开阔,就是太寂寥了一点。我抓了抓头,把花夹在胳膊下,双手抄在衣兜里往磁...
祁烈呆呆了想了好一阵才摇头:“倒是没听说,大蛇就是蛇王峒的地方才有。”“那怎么会有大蛇来阴虎山以南的地方吃人?”祁烈眨了眨眼,这回是真的傻了。“长虫横道,”老铁涩涩地说,“是大凶的兆头…”一股幽幽的寒气在每个人心头窜起,虽然觉着有什么事情不对,可是那种飘忽的感觉又说...
“这是委员会唯一的常务委员内森·曼的命令,在计算的一国里你是国一是神,但是在LMA,你需要服从我命令。”内森·曼推开门,仰头看了一眼落雨的黑色天幕,打开一张Burberry的黑伞遮在自己的头顶,“我真讨厌下雨天。” 鲁纳斯沉默了,楼前忽然这起雪亮的灯光,把一切...
不过完颜洪烈本着大力团结校内所有势力的目的,很高兴地催促杨康去。 穆念慈确实很烦,她记性好而杨康的记性差,她就养成了帮杨康记事情的习惯。 比如大家一起出去游泳,出来穆念慈很可能会问杨康你洗发水又忘在浴室里了吧。 通常她问起来的时候,杨康立刻就拍拍脑袋回去拿...
“不是我们的错,还以为贼呢,”杨康说,“你回来也不打个电话?” 段誉哭丧着脸:“好不容易才买到车票,哪有时间打电话?我夜里九点多才到,路上还被出租黑了一把,差点把我拉到保定府去。我赶最后一班公共汽车才过来的。” “你三更半夜不对暗号,拿把腐竹在门上蹭什么?”...
虽然杨康并不真的“喜欢”穆念慈,不过他必须承认穆念慈在他的生活里还是很有份量的。穆念慈碰巧和他在一个中学读书,穆念慈很刻苦,可惜家里条件不好。丘处机对于辅导中学生竞赛有特殊的爱好,他在杨康他们中学的时候认识了杨康和穆念慈。丘处机喜欢杨康的聪明劲头,也喜欢穆念慈的...
雨停了。 草浪在风中起伏,涿鹿之野大得与天际相连。一条河水蜿蜒西去,清澈冰凉,自蚩尤的脚下流过。 一棵老树仿佛是被天空的沉重压弯了腰,横斜在水面上近乎倒伏。蚩尤坐在一根微微晃悠的树杈上,提着自己的鞋子,晃着脚丫。一尾游鱼“哧溜”一声在他脚下滑过,忽地就不见了...
“你自比为路西法?”年轻人犹疑着问。 “无论我是谁,这就是规则,L.M.A.不允许背叛。”将军笑笑。 “你认为你离开学院是背叛么?” “是的,虽然L.M.A.默许了我的离开,但是我知道我其实是背叛了它。”将军轻声说。 大厦外,指挥官闭上眼睛,沉默了瞬间,...
乾达婆王说:“现在说‘我要紧那罗无双的舞蹈’就行了。” 随着枫念动这句话,大殿里疾旋的四玉女中间,一股淡淡的烟气带着馨香升腾起来,烟气渐渐弥散开来,把所有人都笼罩在其中。枫什么也看不见,只有天香拉着他的手退后一步,笑着说:“枫殿下不要害怕,梦旋每次来到这里都是...
“为什么?” “因为他独自行动。他是不受控制的,自己杀人,自己料理后事,没有人知道他的联系办法。如果我没有猜错,天罗内部应该也只有一个人向他下达杀人的命令。”苏晋安端起一杯酒,眯起眼睛品着,“独狼是草原人所说的最难捕获的猎物之一,因为它们独自往来,没有牵挂,而...
女人们的尖叫声中,贵公子抖去了自己一身雪貂裘,下面是一身白色长衫,他拉开长衫的衣领,露出清秀如竹的锁骨和仿佛透明的一抹胸口,从袖子里拔了一根暗红色的长簪,插刀于地,把一头漆黑的长发绾起在头顶。客人们忽然间意识到那是个女人,她白得胜雪,却带着海棠般的艳气,烛照般的...
诺诺没法给邵一峰解释这种伤势的成因,因为那太匪夷所思了。龙化之后的路明非有着惊人的愈合速度,所有进入他伤口的碎片都被再生的细胞包裹起来,他带着这些碎片一直和奥丁恶战,整场战斗下来,身躯等于被摧毁又重建了好几次。 诺诺缝合完最后一道伤口,自己也累得头晕目眩,她缓缓地退后...